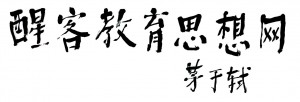作者 | 李倩 发表时间 | 2010-04-20 来源 | 南方人物周刊
第一个到牛津去的中国人叫沈福宗。这已经是1687年的事情了。
在他到来之前,牛津大学里没有人能够看懂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甚至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翻阅。
沈福宗用拉丁语告诉人们应该用怎样的顺序去阅读,并且为博德利图书馆制作了中文书籍目录。在他离开将近200年以后,这里才开始陆续有了中国人的踪迹。
在沈福宗离开牛津大学300多年后,牛津大学已经有超过2000名中国毕业生。
2009年底,牛津中国留学生数目为732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留学生群体。在1996-1997年,这一数字是89人。2010年9月,牛津大学还将迎来中国留学生入学人数的历史最高峰。
牛津大学副校长杰西卡·罗森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牛津学习,但是她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牛津的价值,“牛津大学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著名。”
科学家大卫·库克因
大卫·库克因的一生,没有一篇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自然》、《科学》上,但当他的退休仪式于2009年9月在牛津大学Linacre学院举行时,全世界最顶级的材料学科学家云集于此。
大卫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世界电镜联合会的前主席,因为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不乐观,因此他决定办这个仪式。而形式上,大卫决定做成学术会议。
大卫的合作者,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李国强说,大卫希望用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所有科学家聚在一起,探讨科学发展的新进展,研究科学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
在李国强心目中,大卫是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他喜欢他做的研究,所以他坚持做了一生,“虽然这个研究再做100年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
在李国强和大卫合作的三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还不及他博士最后一年的发表数量。“大卫非常严谨,他对数据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
牛津大学对博士生没有论文要求。李国强觉得,虽然没有压力,但这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因为你的隔壁可能就是这个学科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做。”
牛津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崔占峰也觉得,这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做科研,“你在哪个实验室都可以做实验,你为什么要来牛津做?”
“我刚到牛津时,隔壁是一个老头,个子不高,每天带个头盔骑一个很破的自行车。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牛津大学材料系的创始人。因为当时牛津大学规定,教授65岁退休,就必须把实验室让出来。如果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可以分给你一张办公桌。”
李国强觉得,牛津大学不是一个追腥逐臭的地方。“这里的教授,如果他们想要挣更多的钱,第二天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但是他们不想。”
在牛津3年,李国强说从大卫身上看到了科学的真谛:科学是人们因为兴趣爱好而去做的事情。科学是为了去了解世界,为了改变人类生活。
“思想就像空气,他一直存在,就看你能不能感受到。”在离开牛津后,李国强这样回忆他在牛津的岁月。
导师制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星认为,导师是牛津大学本科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本科生每学期都要完成2至4门辅导课程。尽管按照传统的导师要求,辅导要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但受到辅导教师资源的限制,目前,牛津的导师大多有2至4名学生,同时,一些高年级的研究生也作为辅导教师参与导师。
牛津的学期较短,只有8周,每门辅导课程在学期内进行,每周1至1.5小时,但辅导并不仅仅限于辅导教师和学生见面的这短短1至1.5小时之内。在课程开始前,辅导教师会为学生提供详尽的辅导大纲,为每周的讨论主题提供相应的文献,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主题和文献撰写2000字左右的周论文。学生需要在辅导课程开始前向辅导教师提交自己的周论文,在每周会面进行导师时,辅导的主要内容便是依据学生的论文,讨论对辅导主题和相关阅读文献的理解,辅导老师一般会根据论文的内容准备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对关键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辅导教师与学生的会面,实质上是针对同一主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辅导教师对学生阅读和思考的考核,一方面也是学生和辅导教师对同一主题理解方式的相互挑战。
当然,导师制也受到了一定的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在对其效率的讨论上。导师制是否与现代大学的规模效应之间存在矛盾?高昂的成本与产出之间是否成正比?受金融危机影响,在国家削减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导师制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并保证质量?对于这个延续了700多年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思考也成为了当下牛津大学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般,一次导师课程需要提供给辅导教师的报酬为40英镑左右,加之教学管理上的支出,导师制的运行成本非常高。作为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学院之一的莫顿学院,在英国政府宣布削减2010/2011年度教育拨款后,其网站上公开发表文章,称将继续保持并完善导师制。正如牛津大学新学院大卫·帕尔弗雷曼博士的描述一样,导师制是牛津大学这一高等教育桂冠上的璀璨珠宝。作为自由教育传统中的一个典范,导师制所倡导的思辨精神,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
Balliol
Formal dinner是牛津的传统晚餐。在这一顿晚宴中,教授们坐在高桌上,学生们在台下分列开来。所有人都要穿上自己的黑袍,在一段拉丁文的祷告后,开始依次享用前菜、正餐、甜点。等级不仅体现在座位上,也体现在黑袍上。本科生的黑袍是一件“小马甲”,研究生的黑袍则长过膝盖。校长彭定康也有自己的黑袍,那是一件有颜色的长袍了。在牛津,从每个人黑袍的颜色与样式,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学历与地位。
Balliol是牛津大学所有学院中少数没有Formal dinner的学院之一。原因是,在1965至1978年间担任Balliol院长的克里斯多夫·希尔是一位终身信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要在Balliol这所建立于1263年的学院中消除贵族气息,培养共产主义氛围,因此废除了实行数百年的Formal dinner。之后历任院长均没有再恢复。
希尔在担任院长的13年间,更多的精力是培养了布莱尔·曼宁等后来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学生。当时英国仍是北约核心成员国,其大西洋对岸的盟友美国在后麦卡锡时代继续与苏联冷战。
历史毕竟是历史。在该学院博士生王皓眼里,那次Formal dinner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导致饭堂里的员工都具有了共产主义的特点,无论打饭的队伍排得有多长,他们都无动于衷地慢慢盛饭。但在Linacre学院一位学生的眼里,Balliol的饭堂则是令人向往之地,好吃,便宜,“去年只要2镑,今年涨价了也不到3磅,还有几乎免费的酸奶与水果”。他倒是希望这种共产主义气息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在Balliol对面的汉堡店里,一碗番茄汤的价格也是两镑。
争辩
牛津校报《Charwell》的编辑将讽刺校长彭定康和校务长的漫画刊登在1月29日的第3版。左侧校务长佝偻着身体向彭定康询问如何收费的问题。右侧彭定康口中大呼“学费、学费”,面目可憎,胸前用铁链挂着写有“彭定康”的木板。
事件起因是彭定康在1月中下旬的一次伦敦演讲中提到,从个人的角度,他希望取消英国本土学生学费最高额度限制的政策。
校报立刻作出反应,在1月22日的官方网站头版批评彭定康的想法“非常的荒谬”。
在同天出版的报纸上,校报在第12版整版关注Google和中国的关系,顺便公开质疑“为什么学联里的成员都来自私立高中”,并公布“牛津学生有无使用违禁药品”的调查结果。
牛津中国学联前主席、教育系博士生肖文觉得,英国人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渗透到他们骨子里的东西。
朱继文则亲身在英国议会里感受到了这一特征。朱继文是工程系的博士生,清华牛津校友会会长,其所拿到的牛津中国奖学金每年的活动之一是在议会与下议院议员同进晚餐。他发现英国“国家的价值观跟中国真的不一样。在我们看来都是小事,他们一直在那里吵架。他们这里对平等啊、公平啊,真的很关注。”
杰西卡·罗森说,“我们西方人会以一种很友善的方式进行争辩。实际上,友善的争辩比简单的同意更为礼貌。”
同样是在校报《Charwell》上,牛津大学的一位院长因为不满意前常务副校长约翰·胡德的改革政策,而嘲笑其新西兰背景:“不要以为你在惠灵顿广场办公,就以为牛津是惠灵顿。”约翰·胡德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副校长。不知他对这番嘲笑,是一笑而过,还是只当成善意的争辩。
政治
在这里,中国学生谈论政治话题甚至发表政治言论也并不是无所顾忌的。一位女生曾在一次酒会上告诉在座的所有人注意自己的发言。
但这并不是主流,毕竟这里的信息接收面要广很多,时间久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左派,右派,极左,极右,或者温和派。英国的社会对左右的恐惧远不如曾经有过惨痛记忆的中国。一部分中国学生也无所顾忌地在Facebook上标出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是左还是右。
也有非常善意的劝告。
去年9月的一天,我和朋友逛牛津大街时,遇到一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员。当我介绍自己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实习记者时,他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
次日,这名研究员在街上拉住我朋友,请他务必转告我一段话:“南方报业的思想太XX了,特别是《南方周末》。为了你朋友的安全,还是请转告她,最好离开南方报业。就算暂时不能离开,也劝她不要陷得太深了,及时回头。”
这里也有小政治,比如选举政治。
中国学生很少有人关心牛津学联的主席是谁,但牛津中国学联的主席,所有人都知道。牛津中国学联(以下简称学联)也是中国大使馆在牛津大学设立的唯一官方机构。
在牛津,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学联的成员,只要报名就能加入。但是要成为学联的委员会成员,则需要选举。学联主席团的换届选举在9月份举行。学联共有1000多人,委员会有40多人。
“第二天要选举了,主席团提前一天才告诉我们候选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是张山。”一位前委员会成员这样描绘2009年的换届选举。
代理主席程奇峰的解释是,“我们在委员会里发出通知,征集主席候选人。但我们只收到了一个人的报名表。”
经过选举,张山当选2009-2010年度牛津学联主席。后因张山于2010年1月提前离开牛津回国,所以代理主席程奇峰目前全权负责学联管理,“选举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能因为张山走了就提前选举。这一届,张山还是主席。”
学联目前的主席团选举形式是委员会选举,也就是只有委员会成员有资格选下一任主席以及副主席。在2004年前后,学联曾经尝试普选,即所有学联成员都有选举资格。04-05年的主席赵志强即为普选主席。
在普选实行约3年后,学联又将选举方式改为委员会选举。
剑桥中国学联和牛津中国学联一样,从委员会选举改为了普选,但一直持续到现在。程奇峰在剑桥中国学联的同学非常诧异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普选放开了就不能收回去,你们是如何做到放开普选又收回去了?”
“普选有普选的好处,影响力大”,但是程奇峰还是不希望普选,“因为太浪费时间了”,而且“不能反映出来真实的声音”。 他认为委员会投票比普选更合理,毕竟委员会的人“都在这里面付出过,都有感情。”
张山的前一任学联主席是肖文。这个干练秀气的女生说,“我希望不要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学联。你做这个事情可能不符合那个人的标准,做那个事情不符合这个人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你回国以后遇到的还不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哪里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事情。”
教会
在牛津,教会几乎无处不在。国家公派留学或者访问的师生的第一个落脚地一般都是一栋叫做“Common wealth” 的公寓。这栋公寓属于教会的房产,紧邻Christ church学院,公寓的管理者每周都会邀请住户参加一到两次教会活动。
在牛津市,教会大约拥有20%的房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专门租给学生以及访问学者。相对于私人房屋,教会的房子往往价格更合理,并且能够提供图书室、会客室等公共场所,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也愿意选择租住教会的房屋。
但邢伟始终在思考“为什么教会那么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邢伟在跟着清华大学一位知名中国研究方向教授完成博士研究后,拿了世界银行的资助来到牛津大学做中国国情研究。
“有一个韩国人,叫金,他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邀请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免费去他海边的公寓度假。他只邀请在中国有工作单位的,结束访问后肯定会回国的人。”邢伟琢磨着这个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邢伟来到牛津的前一年,一位清华03级本科毕业的女生来牛津攻读硕士学位。在一年硕士课程结束后,她选择了留在教会工作。
朱继文曾经在一次免费的教会晚餐上见过她,这是朱在牛津3年里唯一一次去教堂,他至今对饭前的仪式记忆犹新,“他们问,继文,你如何看待上帝复活。我说,‘啊?我没有看法。’”
圈子
Jenny说话时非常有激情,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对面的人。
“大的来说,本科生家庭比博士生好很多,不过本科生也基本不跟博士生玩。”Jenny已经开始上硕士课程,所以和博士生也偶尔玩到一起。
“就我们这些本科过来读书也不是个个家里都狂有钱。有官僚子弟,也有大老板,也有小开,也有中产阶级,也有考上以后砸锅卖铁来的。”
Jenny举了一个例子。牛津最贵的中餐厅是上海30。“比如说,大家说去上海30吃饭,刚开始可能大家都去,一顿饭每个人至少三五十镑。但家境不是特别宽裕的去了一两次以后,肯定就不去了,去不起啊。慢慢的,圈子就出来了,差距也就出来了。”Jenny说自己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120磅左右,这个价格不包括住宿费以及衣物购置费。
Jenny是06年入学的,和薄瓜瓜同一届。但是Jenny和同届的中国人很少与薄瓜瓜一起聚会。“毕竟是不同的圈子,他只跟外国人玩。”
“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一位认识薄的博士生这样说,“有一个高官的儿子也在牛津,父亲都被双规了,还是照样开着法拉利。”
薄瓜瓜住在市中心的一栋私人房屋里,因为学院的房子“每年都要学生搬来搬去的,没有家的感觉”。他的坐骑是一辆在12月初时前后轮都没气的自行车。
Jenny住在学院,一室一厅,带独立洗手间。她一般都步行。
Jenny和薄瓜瓜今年都面临毕业。Jenny已经拿到了牛津的博士入学许可。在此之前,她一直试图在英国找份工作,但没有找到。
“我们这一届其实是比较悲惨,中国人,就我知道的40多个,目前还没有人在英国找到工作。不过我们回国工作都很容易找,因为家里能够把孩子送出来,大多都是有一点背景的,回去工作都不是问题。”
杨贵东在牛津呆了也快有两年了,他的圈子和Jenny以及薄瓜瓜没有任何交集。
杨贵东是拿中国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出国访问的学生,因此他不需要给牛津交学费。他的生活费就是每个月国家发的650磅的补助。
“刚开始我住在牛津旁边一个小镇上,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月房租280磅。”后来杨贵东的导师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家庭旅馆做看管门房。他每天晚上从7到12点都需要呆在旅馆里,帮新到的客人开门,为已经入住的客人提供一些帮助。
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但给杨贵东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和一顿早餐。“这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每个月可以省下300-400磅。”杨贵东全年的消费大约4000磅,而牛津大学网站公布的学生最低生活费标准是1.1万英镑。
我们都戏称杨贵东是“牛津华人的第一保安”。
系统
薄瓜瓜喝着冰红茶说,“牛津的中国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而且,你一旦融入到这个系统里以后,你就完全收不到这个系统外的消息。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而且和白人的圈子几乎没有交集。”
薄瓜瓜认识的一位化学老师说,他教的所有学生,最优秀的都是中国人。但是,很多他的学生,来这里三四年了,都不会说英文。
杰西卡·罗森也多次在午餐的饭桌上和导师们探讨这一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只和中国人交流?为什么他们只喜欢讲中文?”杰西卡·罗森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虽然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的进展与西方学生相比要差很多,因此他们的水平要低很多,这是个遗憾。他们用中文交流太多。中国学生不问为什么西方与东方不同。我却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同?他们的秘密何在?因此,中国学生学到的东西不多。”
杨贵东就觉得自己一直无法融入牛津的社会。
“他们总喜欢教训别人,觉得中国人素质低,没理想。他们这里的建筑工人每个月挣2000磅,我们的建筑工人挣多少钱?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们去尝尝吃不饱饭的日子,看他们还说不说。”
杨贵东说自己对祖国有浓浓的依恋之情,所以非常不喜欢英国这个国家。
中国研究中心的邢伟则觉得除了生活,在研究上也曾让他很难受,“他们虽然很认真地研究中国,但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他们的研究都是带着一个救世主的心态。” 邢伟觉得这种惯性思维让他难以接受,“刚开始的时候,我试图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中国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薄瓜瓜认为两个系统的平行是因为中国人的封闭,“黑人其实以前也很受歧视,但是他们很开放,去创建一个自己的文化,让世界看到,所以现在他们并不受到太多歧视。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肤色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融入到那个大环境里。”
祖国
Balliol学院隔壁的Blackwell书店里,萨义德研究“他者”的书以及DVD占了半张书架,很畅销。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至今仍能在中国大部分的书店买到。
北京大学效仿牛津PPE专业开设课程,牛津历史系拉纳·米德教授把他的博士生华沙送到了北京大学做为期一年的交流。4月12日,牛津新任常务副校长汉密尔顿将访华,而牛津大学也开设了中国大学校长交流学习班。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王韬、陈寅恪、吕叔湘、许地山、钱钟书、杨宪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而现在,肖文、朱继文、杨贵东、蒋濛在这里学习,他们都准备在完成学业后回国。
拉纳·米德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学生那么想报效自己的祖国,“在英国和美国,没人会这么想。这是太简单的问题了,但是中国学生一直在这么想。”
“我想,中国的父母们过去没有自由,现在的学生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自由去帮助国家。”
拉纳·米德觉得,自由是问题的根本。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肖文、张山、许平、邢伟为化名。感谢牛津大学所有朋友对本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