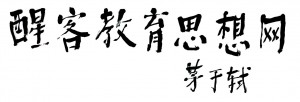作者 | 叶匡政 发表时间 | 2015-08-26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作者授权)

由于对语言管得过宽、过死,一些经过10多年教育的人,天然地反感像高尚、境界等这些高雅的词。网络之所以新词层出不穷,也是这种逆反心理导致的。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天天强调语言、词汇规范的重要,一方面民众急速地向“烂语文”方向堕落,这就是当下白话文和语言的真实现状。
这些年各地的音乐节和艺术节,多有专门的戏曲板块,如北京传统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除上演常见的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外,还会挖掘一些并不常见的地方剧种,如浙江婺剧、湖北汉剧、晋剧、湘剧、滇剧等。这些年看戏的感受是,无论什么剧种,一些传统剧目还可听听,如是新创作的剧目,基本上不忍卒听。连戏曲都无法体现汉语的音韵之美了,这种现象确实应令当代人警醒。前些年去中国音乐学院做个讲座,学校的几个白发老教师告诉我,如今连这种传统音乐的高等学府,也没有专门讲授音韵学的老师了。
中国文化从《诗经》后有一个传统,认为文学与音乐是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文乐一体”。《尚书》有一句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永,就是咏唱、吟咏的意思,可见诗歌也好,音乐也好,“咏”都是一个核心。
所以,《礼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乐器奏出的音乐是跟随其后的。《诗经》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谈的是诗、乐、舞的三位一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乐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也形成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最大不同,就是“语言”之声成为音乐最基本的创作元素。俗话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里的“丝竹”指的就是弦乐器和竹管乐器,认为它们的声音不如人的肉声。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音乐总是效仿人声,并非人声效仿音乐。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音韵构成非常复杂,有四个声调,一些方言甚至有七、八个声调之多。这种独特的发声方式,不仅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韵律,也使它呈现的音乐性与西方语言差别极大。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戏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各地方言的音调与韵律的不同,各地的戏曲形成了不同的声腔和曲调,这也是中国有三百多个地方剧种的主要原因。
汉字音韵的复杂,使传统的音韵学特别发达,和训诂一样属小学。戏曲音韵学研究的是汉字的语音,目的是寻找汉字在文学和音乐中的声音之美和规律,以便最快捷地解决音乐与字音的关系。古人关于戏曲音韵的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代的《洪武正韵》、清代的《韵学骊珠》等,其他的像明朝王骥德《曲律》和沈宠绥《度曲须知》,也都是学习戏曲音韵必读的典籍。在戏曲中,过去有“北宗中原,南宗洪武”的说法,这里的中原和洪武,说的就是两本韵书。只是随现代学术的建立,音韵学尤其关于戏曲的音韵学,竟成了一门绝学。即便是研究音韵学,也多以历史语言为对象,对现代汉语音韵体系的建立和音韵之美的发现,几乎毫无建树。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声音被视为文学的生命,比起声音来,文本的意思有时反而退居其次。但由于古汉语使用的是单音词,古代音韵学也被封存在现代汉语的经验之外。关于汉字的一些音韵常识竟完全与现代人隔绝了。
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不能不说它对文学语言只完成了精神启蒙,但它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汉语声音的忽视和遮蔽。现代文学语言在声音上是完全凌乱的,这从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就可以感受到。当代作家中,除汪曾祺因有戏曲创作功底,文学语言呈现出某些汉语音韵之美外,大多作家的语言在声音上,包括很多现代诗,都是很难找到音韵之美的。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主动从戏曲中发掘汉语声音之美,当代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刘索拉,一个是莫言。刘索拉因本身是一个音乐家,对汉语声音有天然的敏感,她的小说《女贞汤》除政治反思,很重要的就是对各个时代语言声音的模仿。在我看来,这和她近年的人声表演是一脉相承的。小说横跨四千年,其中既有山海经的声音,有明清白话的声音,更有戏曲、诗歌、民谣的声音。可以说,这是中国汉语的各时代声音的一个样本。而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模仿的则是山东高密的民间戏曲“猫腔”,从小说的章节名字,就可看出他对声音的在意: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要恨声、赵甲道白、小甲放歌、知县绝唱等。

这两部小说我之所以认为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声音回归。白话文在1949年之后,几乎失去了和古汉语音韵之间的所有联系。瞿秋白有一句话,说白话文“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人不鬼”,我看还得加上一句,叫做“无声无息”。现代汉语的粗陋,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它的声音上,这已成为60多年来,留给作家最痛苦的文化遗产。这种语言的粗陋,不仅使现代文学远离了声音之美,也使现代文学成为一种反声音的案头文学,蕴藏在中国古诗和戏曲中的汉语声音美学,完全被颠覆了。这是当下白话文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何发现声音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现代语言学一个难题,也成为文学和戏曲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鲁迅说过“无声的中国”,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无声,因为文学中的声音之美完全失传了。
如果追根溯源,与国家对语言的过度规范和管制语言的僵化思维有关。语言和文字的规范虽有利于人们的沟通,但须经过时间的历练。语言规范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和继承,更需有充分的自由,允许它自我发展与变化。只有到新要素积累到一定历史时间,才有淘汰旧要素和规范的必要。1949年后,因对语言规范工作做得过于苛刻,完全不尊重语言自身的规律,已使很多地方的方言濒临衰落或消失,普通话从方言中汲取的营养也越来越少,语言多元、进化的迹象几近停滞。
由于对语言管得过宽、过死,一些经过10多年教育的人,天然地反感像高尚、境界等这些高雅的词。网络之所以新词层出不穷,也是这种逆反心理导致的。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天天强调语言、词汇规范的重要,一方面民众急速地向“烂语文”方向堕落,这就是当下白话文和语言的真实现状。
白话文和普通话最主要的源泉,是各地的方言。方言土语是汉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然而由于不允许在电影、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上使用方言,使今天的普通话,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都变得越来越枯燥贫乏。普通话如果失去方言的滋养,就成了无源之水,它毕竟不是天然语言,而是人造语言。方言的生动性,是普通话永远无法抵达的。我们看到,小品和电视剧一旦使用方言,总能受到观众热捧。
过去中国戏曲的发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方言的运用。因为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声韵之美,会形成不同的声腔和曲调,此外,方言蕴藏了大量民间智慧,语言之美只能从生活中得到发现和创造。可设想,假如明清时代,朝廷也有一纸禁令,要求所有戏曲全统一成华北官话,今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之多的地方曲种了。这是语言学的简单常识。
保护濒危方言,保护汉语的多样性,重塑汉语的声音之美,最重要的就是要取消对语言的过度规范。让语言在各类艺术作品中,有自由呼吸和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