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洪彬 发表时间 | 2013-06-16 来源 | 东方早报
■ 道德滑坡和核心价值的问题,确实是当代中国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是企图以课程设置的方式来拯救道德,恐怕是缘木求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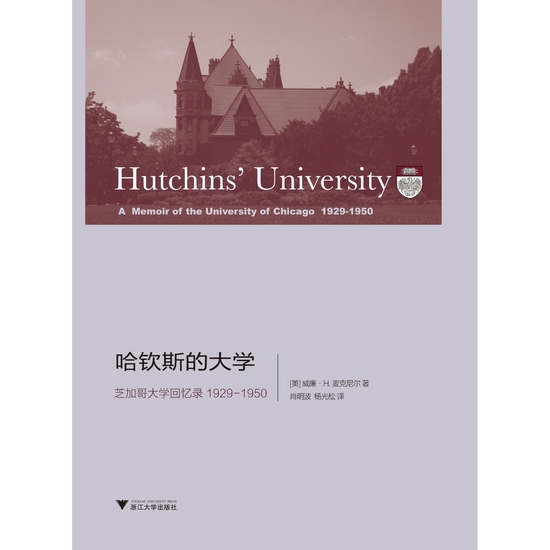
《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
[美]威廉·H. 麦克尼尔著肖明波 杨光松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一版379页,45.00元
1929年,年仅三十岁的哈钦斯开始执掌芝大,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在哈钦斯入主之前,芝大的招牌是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而其本科教育一直停留在比较低下的水平。但在他主政期间,芝大的本科教育水平提升很快。很多人把这种成绩的取得归因于哈钦斯开展的通识教育实验,但是麦克尼尔所著《哈钦斯的大学》认为这并非实情。麦克尼尔是一流的历史学家,鼎鼎大名的《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文明之网》等均出自其手;更为重要的是,哈钦斯主政期间,作者是芝大的学生,后来又长期任教于此,在写作该书的时候,阅读了大量档案材料,对实际情况相当了解。因而,他的观察和理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作者指出,哈钦斯的通识教育方案,直到二战时因种种内外因素才得以实现,且取得的成绩远没有哈钦斯所希望的那么大,通识教育得以实施之后的芝大本科生院“从来没有像哈钦斯期望的那样,起到美国教育标兵的作用”(第247页)。在他任期中,芝大本科教育质量和名声的大幅提升,更多是得益于本科生院院长鲍彻设计并推行的教学改革,其内容主要包含大力打造基础学科的概论课程,设计全新的考试体系,允许学生自主设计培养计划。再加上芝大在媒体宣传和招生方面取得的成绩、因避战而从欧洲前来的优秀师资力量、对种族问题的开明态度等因素,芝大本科教育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之芝大“本科生院成功的秘密和核心,注定了哈钦斯的希望会落空。本科生院之所以如此出色,是因为它集中了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才智和严肃目的,并得到了才华与专注相对集中的年轻教师的支持与维护”(同上)。
当然,哈钦斯的个人魅力、公共名声及对时代问题的敏锐回应,使大学教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从而对芝大的名声和招生工作大有助益。这也是哈钦斯被芝大人念念不忘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哈钦斯的努力迫使人们去思考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世俗时代的教育,是否应该去回应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世俗时代的人们应该怎样才能建立和平共处的思想共识?很多人觉得哈钦斯主政时期的芝大是一个黄金时代,作者认为哈钦斯的成功应该“以他激发和维持各种刺耳的声音的非凡方法来度量”(第287页),在这个意义上,那的确是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把芝大本科教育提升归功于哈钦斯的通识教育,并不符合事实。鲍彻大力强化的概论课是强调专业基础的,与哈钦斯反专业主义的通识教育理念可谓南辕北辙。最为尴尬的是,通识教育本是为那些不打算继续从事专业深造的学生提供的,“但是它的毕业生都涌入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而不是作为已完成正规教育的普通公民走上社会”(第247页)。哈钦斯主政期间芝大成立的社会思想委员会,非常重视跨越学科边界和原典阅读,这似乎与哈钦斯通识教育理念最为接近,但这里显然不是一个培养普通公民的场所,而是学术精英的摇篮。这也许意味着,跨学科和原典阅读是精深研究的利器,却并非初级阅读的理想选择。
该书最具新意的是从哈钦斯的成长背景来理解他的通识教育理念。哈钦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长老会牧师。长老会相信救赎并非来自盲目而狂热的信仰,而有赖于对上帝旨意的理解,因此“知识和真理”才是最重要的,而牧师的职责就是提供这样的真理和知识。但是因为个人阅历等因素,哈钦斯放弃了他父亲寻求真理的道路,“并在余生中试图寻找一个东西,来替代他父亲的《圣经》”(第48页)。这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判断。阅读哈钦斯集中论述通识教育理念的《美国高等教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教育的理解,与宗教信仰的失落之间构成了多么密切的因果关系。哈钦斯认为,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一是为人们的事业做准备。在他看来,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科学家和学者,大学应教给学生真理。他相信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汪利兵译,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5页)。而“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教育的内容也是普适的,“面向全体人民的课程的核心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都将一样”。他甚至认为“教育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和地方生活,或调整他们适应特定的环境的观念,是有悖于真正的教育理念的”(《美国高等教育》第39页)。通识教育不仅主张教育的内容是普适的,适用的对象也是普适的:“通识教育对大学生涯是有用的;但如果不进大学,通识教育同样有用。”(《美国高等教育》第37页)
那么,这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哈钦斯知道中世纪大学的真理是神学,可是神学教育建立在天启和信仰的基础上,而“我们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不相信天启”,他于是转而求助于古希腊思想的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探究的是事物的最高原则和起因”,是“最高层次的智慧”(《美国高等教育》第56-57页)。哈钦斯急切寻求的是如他父辈的《圣经》一样的替代品,那是一种适用于世俗时代的确定的、统一的意义和真理。他宣称,如果教育不以意义的追求作为首要的目标,大学就变成职业培训的场所,意义和道德付之阙如。1935年他在对毕业生演讲时说:“我不担心你们将来的经济状况,我担心你们将来的道德状况。”(第131页)显然,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仅仅懂得形而上学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哈钦斯还加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教给学生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哈钦斯的通识教育实验、学习型社会的倡议、名著出版工程都出于这个理念。
哈钦斯的整个任期,都竭力推进通识教育的开展,但是一直遭到大多数同事的反对。许多教授认为让老师和学生花费一两年时间来学习与专业深造无关的知识,是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哈钦斯推崇的真理和理性遭到了强有力的抨击。他的一个主要反对者哈里·吉第昂斯就不相信有一种统一的真理存在,相反,“不受约束的真理之争”,尽管可能是混乱无序的,却是对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支持(第133页)。麦克尼尔也指出:哈钦斯所推崇的形而上学和理性并不足以确保他一直渴望的东西——“一组关于对与错的明确规则”(第132页),在经典名著中寻找的“统一的真理”,自身需要理性来加以判断,但是如果有理性的人出现分歧怎么办?更何况理性本身已经需要论证。对此质疑,哈钦斯没法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是,哈钦斯主政芝大期间,引进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巨擘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的思想主旨建立在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他批评现代西方人已经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已经不再相信他能知道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对和错,而应对现代性的危机的方法是“恢复那些关于对与错,正义与美好的根本问题的地位”。施特劳斯相信,“真理”主要是从古代哲人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求。这一点与哈钦斯的观点相当合拍。以赛亚·伯林曾指出:施特劳斯相信“善与恶、对与错都直接得自某种先天的启示,某种‘形而上学之眼’”,古代哲人都通晓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伯林语带讽刺地说,这样的“魔眼”恐怕只有极少数精英才具有,自己无缘分享。对于施特劳斯向“传统”寻求“真理”的主张,伯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并不是唯一的。在相互冲突乃至无法调和的传统思想之间,怎样才能找到一种统一的真理?
同样,哈钦斯相信中世纪的神学是一种统一的、客观的真理,他似乎忘记了神学自身也是派系林立,也忘记了宗教战争的惨烈,而这正是西方社会世俗化的动力之一。哈钦斯认为古希腊比中世纪离我们这个时代更近,因而企图以形而上学来替代《圣经》,但是他所推崇的伟大哲人之间的分裂和敌对,不啻于另一种宗教战争;更何况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西方社会以外的哲人经典是否应该成为每个公民都应知晓的思想资源。哈钦斯的通识教育实验,是世俗时代追寻统一真理、确定性和意义的失败尝试。他及其同道中人对形而上学的追寻,宛如一曲献给上帝的挽歌,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绝望与忧伤。麦克尼尔说他像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是个注定失败的英雄。他设想的大学,正如他的一本书的标题,是“乌托邦大学”。哈钦斯在去世前不久甚至说:“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失败的。”(第285页)
毫无疑问,麦克尼尔给热心通识教育的人泼了点冷水。我认为这点冷水对当下中国也可发挥一点镇静剂的作用。近些年中国知识界对通识教育的热情方兴未艾,大体而言针对的主要是:专业主义和学科细分、道德滑坡和核心价值缺失、全球化与文化断裂。首先,甘阳教授就认为,哈钦斯对美国高等教育专业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适用于我国现在的情况”(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4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是受苏俄课程论的影响,中国本科教育还是比较重视概论课和通史课;专业细分主要还是体现在研究生阶段。其次,道德滑坡和核心价值的问题,确实是当代中国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是企图以课程设置的方式来拯救道德,恐怕是缘木求鱼。道德和教养主要是在日常生活熏染出来的,是家庭和师长以身作则“做”出来的,以及法律等惩恶扬善的社会机制规训出来。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的课程中,已经包含了太多道德说教的内容,对于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未见有何助益。
而今倡导通识教育的学者,往往冀图以共同课程、核心课程的方式来把他们支持的学说或方案,变成“那一个”,而不是“其中之一”。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西方国家居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对非西方国家肆行宰制与剥削”,作为儒学学者的他主张通识教育应回归经典的思想世界,寻求东亚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主体性。主张通识教育最力的甘阳教授,坚持本科生应该必修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核心课,而不是“选修”人文课程;他反对概论课程,而力主原典阅读。这两点和他推崇的哈钦斯都很一致。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倡导的通识教育似乎不是要培养普通意义上的“公民”,而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而中国的精英首先就是对中国文明有充分自信的人,因此在他设计的五门核心课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占了三门,分别是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大学古代汉语,另外两门则是外国人文经典和外国文明史。不知道甘阳教授是否像哈钦斯那样考虑过让大学生也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不知主张“通三统”即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的甘阳教授,会把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放在哪一门核心课程里?中国古代文明中,孔夫子传统虽然重要,到底不是全部,何以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小枫教授的学术旨趣在于“古代性”反思和超越“现代性”,因而在他编的通识教育读本中,施特劳斯就成了最为重要的思想门径。正如高峰枫先生指出的,刘小枫先生“大约想让一切有志研究西洋古籍者,必须先进施特劳斯这道‘窄门’”。他还指出,“编者既慨然以通识教育为己任,便当了解‘通识教育’不能是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的‘灌输’。”(高峰枫:《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上海书评》2008年12月6日)这句话我觉得适用于当下中国提倡通识教育的许多学者。
公正地说,通识教育倡导者所批判的问题,大都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的确是我们时代的普遍困境。其中,他们批评最力的西方现代性的确问题多多,古典思想在某些方面也许确实可以补足现代性的缺陷。问题在于,无论是“东方性”还是“古代性”,本身与西方现代性一样,都是充满争议的一家之言,其被认可度可能还不如后者。通识教育的前提应该是已经形成共识和核心价值,而不是把一家之言塞入通识教育来形成核心价值。价值多元已是客观事实,在此语境中自主选择应该成为首要原则。更何况通识教育本身也和宗教一样,只是其中一种颇有争议的方案而已。合理的做法是,让信仰宗教的人“选择”他的宗教,让希望从经典思想中寻求启迪的大学生去“选修”经典阅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