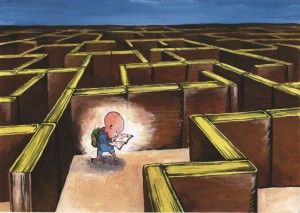作者|刘道玉 发表时间|2011-03-01 来源|《同舟共进》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后,我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进入转型期,这是相对于80年代的大学教育而言的。高等教育转型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即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
25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这就是说,变化是绝对的,但变化是双向的和可逆的,既可以向好的方向变,也会向坏的方向变,甚至还会走回头路。好与坏关键在于把握住高教转型的方向,沿着正确的目标前进,这就要求教育部门领导人拥有智慧。
高等教育的转型,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各项规律。高等教育的规律包括外部和内部规律,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高等教育内部的规律,包括教学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规律,教师与学生按一定比例配备的规律,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相互制约的规律等。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是互相影响的,外部规律一旦受到破坏,势必打乱教育的内部规律,反之亦然。本来,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正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原理之一。可是,我国教育当局的决策人,却恰恰违反了这条重要的教育规律。下面,不妨剖析我国高等教育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一 、 在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中,犯了冒进的错误。例如,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平均增长为8.25%,但1999年大学招生人数较1998年增长了52万人,增速高达47.4%;2000年增速是38.16%,2001年是21.61%,2002年是19.46%;2003年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1000万人,大学毛入学率已达17%,一举提前8年(原计划2010年达到15%)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它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多需要半个世纪,例如美国1900年毛入学率为4%,到1954年达到16.2%,实现大众化用了54年,欧洲大多数国家也都花费了半个世纪,而英国则花费了100年以上的时间。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是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比西方国家晚了大约800年,无论是师资还是办学条件,都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没有能力超越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如果一味坚持跨越式发展,势必降低教育质量,造成大量的毕业生不能就业,也浪费了巨大的教育资源。如果我们按照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速度扩招,保持在10%左右的速度,则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又不致造成大量毕业生就业困难。
二、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犯了片面追求豪华和铺张浪费的错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现代化的旗号下,进口齐全的先进仪器设备,大肆扩展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追求豪华装修。据知情人透露,我国列入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无论是校园面积、豪华建筑,或是先进的仪器设备,都已超过世界上顶尖大学的水平,可是却欠下了2500亿的高额债务。而且,在征地和大兴土木的同时,又每每涉及招投标中的行贿和受贿,使高校贪腐案件频频发生。
三、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自1992年开始了狂热的大学合并运动,持续了10多年之久,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大学。这完全是长官意志驱使下的行为,犯了瞎指挥的错误。当时倡导合校的理由是,实行“强强联合”,以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幌子,是歪曲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和经验。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既不是巨无霸的“航母型”,也不是学科齐全的“万能大学”。实际上,建一流大学是假,好大喜功是真,某些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政绩,竟不惜牺牲大学的根本利益。这次大学合并运动,是1951年以剥离为主导的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全盘苏化”,其专业化教育的副作用持续半个世纪还没有消除;而这次大学合并的弊端和隐患,也将持续50年以上,历史将会检验它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四、大学改名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典型的虚荣心和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中国古人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我国大学改名之多,可谓世界高等教育界的怪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改名一直没有停止,除了极少数几所老牌大学以外,几乎每所大学都改名了,有的则是一改再改,最多的是西南交通大学,竟然改名18次,真可以进吉尼斯纪录了。有人问:“究竟是谁在折腾大学?”我说是教育部,大学改名就是从教育部直属大学开的头,它隶属的工学院先改成理工大学,后又改成科技大学。接着,各部委、各省市的大学也都改名了,反正内容涵盖越来越广,名称也越来越大,从地区名到省名、大区名,直至冠以“中国”为止。这些学校改名都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有的甚至是由教育部主导的,这不恰恰证明了是谁在折腾大学吗?大学改名是虚荣心的极端表现,背后是名和利作祟。大学升格了,名字改了,但水平没有提高,岂不是换汤不换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法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等,几百年不改名、不升格,并没有影响它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五、冠以各种名称的学者满天飞,这是以名和利误导学校的教授。1992年,香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教育部签订协议,双方共同出资1.2亿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促进教师队伍的提高。长江学者的设立,具有特定的意义,但不可把它无限推广,更不能庸俗化。由于各大学虚荣心作怪,于是模仿设立冠以各种山水为名的学者,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珠江学者、赣江学者、闽江学者、天山学者、湘江学者、长白山学者,等等,据我统计竟达38个之多。反正哪里有名山秀水,一定有一个以山水命名的学者。学者就是学者,教授就是教授,冠以山水的名称就能提高他们的水平和知名度吗?这纯粹是搞命名游戏,除了把教师引向追名逐利的错误方向,别无任何积极意义,既导致大学教授之间的不公,又将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笑柄。
六、大学管理机构胡乱改名,再次显示了大学的浮躁作风。以科研管理机构为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的科研管理部门叫科研科,80年代升格为科研处,90年代又升格为科技部(部长与国家的部长混同),现在又更名为科学技术研究院。这是由上海某重点大学带的头,于是一哄而起都改成科学技术研究院了。什么叫研究院?它是纯粹的研究机构,有实验室,配有研究人员,接受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的研究院满天飞,什么WTO学院、市长学院、边界研究院、徽学研究院等,某些大学各地校友会都扯起了研究院的牌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始作俑者,也许是想让大学里的科学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平起平坐,以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
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方法是模仿和趋同,习惯于跟风跑,只要有一个大学带了坏头,于是纷纷效仿,生怕自己吃了亏。大学改名、系改名和管理机构改名,都是循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现在,中国大学里的系统统升格为学院了,可是国外那些最著名的大学,甚至发明了计算机,获得基因和超导重大成果的大学,依然还是叫计算机系(甚至电机系)、生物系和物理系。这说明中国大学追求的是时髦外衣,而不是用心做学问,以这种浮躁作风怎么能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20年了,但我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转型。与80年代相比,教育经费、大学规模、教学与研究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办学思想、教学质量、学风和改革精神反而大倒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坦率地说,我国高等教育现在依然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牺牲质量换取数量的发展,以牺牲学术换取经济利益,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目前,我国大学拥有诸多第一——大学生在校人数世界第一,在读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豪华的校园和楼房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型先进仪器第一,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很快也将居于世界第一——但是,这些“第一”有什么用呢?它们的利用率并不高,除了满足虚荣心和宣传作用以外,并没有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和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二,按照“高、大、全”的思维惯性办学,思维方法依然停留在第二次浪潮时期,这是与第三次浪潮“小就是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小型的高水平大学,多年以来,它与哈佛大学并列第一,该校没有美国最吃香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校长雪莉・蒂尔曼就是不建立这三个学院,集中力量抓好该校的特色学科数学和理论物理。在这座象牙塔中,安德鲁・怀尔斯教授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创造了奇迹。
第三,教育部以“工程思维”(或计划经济思维)指导全国的高等教育工作。在这20年中教育部制定的各种工程、纲要或计划,多达37个。实践表明,计划统得越死,办学者越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必然导致我国大学没有个性和特色。在高教领域,缺乏独立自主创新的成果,很多时候是模仿国外的研究方向和做法。没有创造性的成就,我国高教就不可能转向集约型。既然计划经济不能使我国经济转型,难道计划教育能够使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吗?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混乱,从而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主要原因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教育产业化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当问题出现以后,教育部的领导出来否认,说从来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人们记忆犹新,当初国家某些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频频发表谈话,说教育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不明明是教育产业化的主张,怎么能够否认呢?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即使现在仍在推行教育产业化,如大肆建立科技开发园,在各地建分校、研究院,办各类高价培训班,推行“产学联”的办学经验等,都是教育产业化的表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必须以改革为先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不浮躁、不浮夸的严谨的学风,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维护质量第一的原则,重在独立自主创新,提高办学的效率等,这些才是转型的正确方向。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深刻指出:“当大学决心实行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我们虽然不能把她的话扩大到所有的大学,但对于那些重点大学而言,必须远离功利主义,树立以学术为终身的志业,安贫乐道地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专注于研究影响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并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我想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国才会有能够培养出精英、翘楚和大师的一流水平的大学,也才能完成我国大学真正的转型。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给刘道玉校长的一封信
□ 金振林
尊敬的刘道玉校长:
你好!近阅大作《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方向》(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一口气读了两遍。在短短5000字中,你以翔实的资料,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剖析,涵盖了多么沉重的内容,真是痛快淋漓。多年来,郁积胸臆的对“教改”的深恶痛绝,似一吐为快,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一针见血,可谓大快人心。
我是个作家,曾任《小溪流》杂志主编、《法制月刊》总编,似乎与教育不搭界,可是这些年来,教育界(不仅是高校)的倒行逆施,真正让人愤慨不已。
教育来了个“大跃进”,大学、学院遍地开花。就拿湖南来说,原先有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名校,后来统进了“中南大学”名下,湘雅医学院变成“中南大学湘雅医科大学”;就在马路对面,又有一家“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各系改成学院,各地区的师专一律升格为理工学院或科技大学,真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诚如你文中所说:“建一流大学是假,好大喜功是真”,“大学改名是虚荣心的极端表现”,“名字改了,但水平没有提高”,“欠下了2500亿的高额债务”……
诚如你警告的:“这次大学合并的弊端和隐患,也将持续50年以上,历史将会检验它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旧社会有句俗话: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把它改成:“大学校门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教育产业化最直接的恶果,是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贫寒子弟(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及农村山区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之外。我讲话是有根据的。
最近七八年,我在浏阳石柱峰山区半山腰深入生活,写作长篇,亲眼看到许多山村孩子失学,家庭连温饱都难,哪有钱供孩子读书?许多孩子小学未毕业,男孩去当苦工,女孩(长得漂亮的)便到城市的美发店服务,此地乡民称她们是“卖大腿”挣钱。我有两个邻居,83岁的毛冬生,一家靠养50只黑山羊,百十只土鸡,每年收入一万多元,供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学生读书,负债累累;另一中年人喻自立,夫妻俩到了冬天便包山烧木炭,小女儿小学未毕业,烧一窑才够她的学杂费;大女儿读大学,要七八窑才够用……这两家还算好的,可那些无能力搞副业的农民呢?只好望“门”兴叹,别说大学的校门,就连中学的门槛也迈不进。
中国教育有优良传统,诚如孔子所言:有教无类。以我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读初中是全额助学金,每月7元,月底还可分些伙食尾子,买点糖果饼干之类回家孝敬爷爷奶奶;读地质学校时,更是全由国家包了,连每月的牙膏牙刷、配眼镜也都由学校补助。那时国家只要你安心读书,吃穿都不用你操心。
可现在呢?教育部门把自身的职责忘却了,九年义务教育制也名存实亡。君不见,长沙的几所重点中学,初中部均不招生,而是另起炉灶,在校外与开发商合伙(学校出名称和师资,开发商投资,赚钱分成),办了许多戴帽子中学,动辄收费上万元,把义务教育的后三年“私有化”了,成为敛财的手段。这些难道教育部不知道吗?不说是它规定的,起码它是默认这种做法。
讲的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我是个穷苦人家出身、靠助学金成长的人,我不能在人民疾苦和社会不公面前闭上眼睛。刘校长,因看了你的大作,我才推心置腹地与你交谈,不当之处请予体谅!
金振林
2011年4月25日于浏阳茶子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