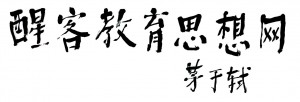作者|唐小兵 发表时间|2012-05-01 来源|《同舟共进》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该校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发表《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在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校庆话语中,因其反思力度和强调大学对国家和公共文化的责任,而显得独树一帜、引人注目。2011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刻,传媒纷纷从不同视角纪念这所寄托着百年强国梦的著名学府,清华在校大学生蒋方舟致校方的一封公开信,更是在网络世界激荡起强劲的公共讨论,它对清华的反省与批评,得到了校方的积极回应,让公众感觉到百年名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与谦卑。教育家刘道玉、学者刘再复等都发表文章,期待清华以校庆为契机,提振人文之精神,思虑大学之责任,规划它在转型中国里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成为20世纪中国关于大学的经典定义之一。究其原意,乃是强调所谓大学,应该是蔡元培所言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空间,这里聚集着一群真正意义上的智者,不为权力裹挟,不为世俗牵引,也不为名利所压迫,他们对科学探索、学术求真、智性交流有着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与想象力,他们对国家、人民有深厚的情愫,却并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政治参与,而是为国家建构和政治转型,提供持续而富有洞见的精神养分。
梅贻琦所言大师,其意义肯定不仅是指清华大学通过对各种资源的吸纳,引入世界其他大学的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而是指应该注重通过自身学术空间的营造,提供让未来大师生长的土壤。校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怀旧、回忆这种初级阶段,而更应创造一种机缘,让清华人以及关注清华的公众获得一种反思平台和开辟新的未来想象的空间,这样的校庆才能摆脱乡愿的气味,才能脱离装阔显摆的窠臼。
这些年,出版界涌现了一批跟民国清华相关的书籍,只要对于这些著作稍加检阅,就可以探测到支撑起老清华大学的大厦,无非下述几个侧面:
学术自由,其标志是教授委员会的教授治校制度,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苦心孤诣的教授们仍力图捍卫学术的自主性和自由特质。萧公权在他回忆清华的文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最可惊异的是,哲学系的教授张申府竟在教室里吹嘘某某主义,为他们做宣传工作。张熙若对他大为不满,在全体教授会开会时,提议检讨张申府授课的情形。在确实判明某某主义和张先生所授的课程没有显明关系,他讲某某某并不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单纯的主义宣传之后,全体教授同意警告张申府,如不终止宣传,下年将不续聘。”可见当时清华教授坚持学术自由的精神氛围。没有这种自由气息,清华不可能在30年代几乎达至其学术的顶峰状态。
民主文化,其标志是学生除了致力于学业外,也通过日常方式进行民主能力的训练和民主习惯的养成。作为政治学系学生(后来成为政治学系教授)的浦薛凤在事隔多年后,仍对清华民主性质的课程记忆犹新:“清华教育重视组织,亦即同时着重‘群育’。以言课程,在中等科时即有‘议事规则’一课,详述主席、发言、提案、辩论、表决、复议等等应守之程序,此盖民主社会中人人应知应守之公正议事规则。”老清华精神的可贵就在于,她将民主规则和民主文化通过“公民课程”的方式深深根植于青年学生的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之中。清华之所以能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众多的政治人才,便与在校期间的民主训练息息相关。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有一句著名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其实,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其来有自,在清华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体育精神和体育训练。这与中国汉代以后知识人的传统格格不入,但在传统私塾教育中成长的读书人,却往往感激于这种新式学堂的体育精神。清华给中国的大学开创了一种清新质朴的新传统,而这种新传统,与传统中国的书院所象征的人文精神并不相背离,汇聚了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为显例,这是一种中西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几近完美的结合。
老清华的这三种传统,在建国后的院系调整等一系列历史变迁与政治运动中备受摧残,也就第三项尚得保留。如今的清华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政府与民意压力下,除了派遣各路考察团去西方一流大学取经外,也应更多地追溯老清华的历史,研讨其成就非凡的内在机制。此时此刻,清华不能仅仅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目标,更应提出对转型中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乃至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1931年的《清华周刊》发表过一篇《谁负知识界领袖的责任?》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等名校教授应该担负的社会角色:“最高学术的教授,有接受新文化的境遇,有研究的时间,如果只知闭门研究只知按时上课,决不算尽了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上所负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特别努力,用著述或讲演的方式,随时供给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正确的(即客观的)报告与评论;在他一方面,也应阻止荒谬的敷浅的知识来妨害社会之进展,来耗费社会之精力。不幸事实的发展,竟向着相反的道路进行!中国的知识界需要他们来领导,而他们则避之惟恐不及,以致知识界陷于混乱敷浅的状态。其直接的影响,为知识饥荒为学术饥荒;其间接的影响,为新中国之实现一再延迟。”转眼80年过去了,新中国仍处于艰难的转型中,知识界的大多数迅速地逃入犬儒主义的泥淖,或者干脆移走异国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最需要的是一批有着公共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社会精英,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洞察力,养成了民主习惯,对中西文化传统有着不倦的探索激情,是一群韦伯所言政治上成熟的群体。他们对于沟通中西方文化传统、促进中国往人类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道路上稳健前行,有着一份义不容辞的担当情怀和责任意识。
在一个高等教育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清华大学不能因此而放弃培养智识贵族和精神贵族的责任。贵族不是见利忘义的暴发户,也不是首鼠两端的政治投机分子,更不是迎合大众的违心之徒。跟贵族相匹配的是文化情怀、政治意识和公益精神,尤其是文化上的创造能力和经典的生产力。清华应该积极创造让贵族能够产生的校园空间,让未来的精神贵族不再受到追名逐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和异化,也让他们能够远离意识形态的规训,自发生长出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世界。
清华有培养科学家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更应通过清华人的努力,扩散到中国的公共社会,并养成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即不盲从权威和权力,服从探索真理的内心自由。更应将这种科学精神弥散到一般民众,让科学的求知精神,真正地点燃普通人的知识之火。没有大众对知识、教育和文化等精神生活的形而上的兴趣作为底盘,没有社会中坚力量日滋月长的个人之理性自觉和人格自觉,即使再优秀的清华人,也无法将其职业理想和政治关怀,建筑在有活力的地基之上。即此而言,今日清华面临的任务是多重的,既有重建和张扬科学理性,摒除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的时代使命,又有复苏老清华的人文精神的历史责任,这样的清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反哺和滋养中国社会。清华本是美国庚子赔款返还部分创建,她从一开始就有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血统,而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又接受了来自中华文化的灌溉,在抗战过程中,更是受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浸润,这多种精神传统造就了清华的传奇。
在这样的意义上,清华校方不能含糊地表示文科是清华的一部分,而更应该指出,没有这种人文主义传统的重构与扩散,没有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洗礼,即使在科学的世界,清华也不可能走得太远太稳。
清华大学东门山坡上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镌刻着史家陈寅恪的挽词,其中的一句话,值得在此时此刻重温:“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若要追溯清华之魂和大学之道,则非陈寅恪先生此论莫属!只有这样,才能告别韦伯所警示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物欲时代,才能以清华人为典范,重建人的主体性乃至中国大学的主体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